武汉大学机构用户,欢迎您!
母题是构成主题叙事的意象、题材等基本元素以及具有修辞性的意义。探讨中国传统艺术母题、主题与叙事的关系,是建构中国传统艺术母题与主题学体系的逻辑条件之一。艺术母题不是偶然孤立的现象,它应该是贯穿了历时性的集体认知,在绵延变迁中所发生的特殊价值具有建构艺术主题学体系的意义,历时性演变的母题可能还是共同意境与主题叙事之源,即原型。因此,艺术作品的母题、主题不仅在同时性也在历时性的叙事演变中绵延呈现,从叙事的视角出发探讨母题、主题叙事的变迁,再返回到艺术主题理论层面的探讨,此结果便是建构母题与主题学体系的基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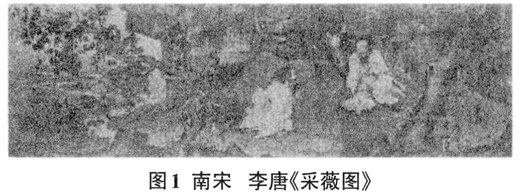 艺术主题以“形式”这个“现象”在叙事中得以展示的。艺术形式不仅涉及艺术形象及所呈现的母题,还指涉艺术结构,如绘画的图式结构、色墨结构、音乐的旋律结构等。如果艺术主题一定要在叙事中才能得到确认,那么,叙事就需要母题、意象、题材以及结构等基本要素才完成。即艺术母题、意象、题材等在一定的图式结构中才构成叙事。换句话说,叙事是母题、意象、题材在某个逻辑展开中表述已经发生事件的独立结构,有了这个“独立结构”主题才能被清晰地揭示出来。由此看来,艺术主题与叙事是密不可分地存在于同一图式结构中的两个相关联的逻辑主体,一些没被显示的主题却会被暗示或隐喻的“空白”由观者进行补充或阐释,使“已经发生事件”的叙事趋于完整,这便是主题学、母题学所要从事的研究工作。李唐《采薇图》作品中两个人物形象是确定的,分别为伯夷、叔齐,图中石壁上著款有“河阳李唐画伯夷、叔齐”。背景“首阳山”则基本上是用山水图式暗示出来的特殊语境,因为这里的“山水”图式没有任何特质可以被认为是“首阳山”的地貌,但是可以通过观者补充完成它指涉“首阳山”这个特殊的“山水”语境,这补充的依据是提款的内容和图像中出现的挖掘工具和藤编篓,藤编篓里还有类似蕨菜叶(野薇菜)等母题元素,暗示着画中人物处在特殊的“山水”语境中,这既是《采薇图》绘画作品的图式结构与母题结构,同时也显示了《采薇图》主题的叙事结构。图画中伯夷、叔齐二入席地对坐,目光交流,似有对语,这也可以看作是《采薇图》中“情节”细化的一个母题性结构。但是这里的山水语境只有在确定了人物身份以及相关母题的出现时,“特殊语境”才可能产生明确的母题意象,否则这里的山水图式与中国传统山水画几乎没有区别,所以我们说它是暗示性的,需要观者补充或者阐释者去阐释才会有清楚的叙事逻辑结构。当然,这里还有两个母题是作为观者补充的重要细节元素,就是画中出现的类似于新石器时期水平的挖掘工具和藤编篓,它直接暗示伯夷、齐叔二人“采薇”这个情节,这个细节化的“情节”观者还可以无限补充,可以看作是绘画视觉叙事的细节化母题,也是暗示“山水”为首阳山的细节母题。一幅绘画作品的主题有着多个母题连接并存有其无限细节化的可能,这便是主题与叙事的同一基本结构。我们也可说这是绘画艺术主题以视觉方式叙事的主要特征,但这些母题、意象在图式结构中不是任何可以返回的时间动态元素,而是在结构中处于“静止”状态的,于是“静止”状态的母题、意象在结构中就有了“空白”(某种意义上与山水画的空白类似),就是说绘画作品的视觉叙事还需要观者的补充或阐释者的阐释,如同我们阐释山水画的“空白”一样,因为“在各种事物之间存在着实际上可以想象的细节的无限连续体,它们通常没有表达出来,但却‘可能’表达出来”[4]12。绘画作品中所谓的“通常没有表达出来”的是绘画艺术特性决定的,受制于绘画的“空间”因素,它们不同于“一本连环画或一部电影,都能毫不费力地转向接近长镜头并返回来”[4]12。这里就涉及我们通常说的“空间艺术”与“时间艺术”差异问题(中国长卷绘画图式另作别论)。《采薇图》需要通过对“图像”中人物(二者之间的关系)、首阳山(实际需要经验补充完成的)、藤编篓和简陋的挖掘工具等母题(实际已经成为意象),并借助“已经发生事件”的文本或传说来帮助完成叙事,从而使观者真正理解《采薇图》的主题表达。
艺术主题以“形式”这个“现象”在叙事中得以展示的。艺术形式不仅涉及艺术形象及所呈现的母题,还指涉艺术结构,如绘画的图式结构、色墨结构、音乐的旋律结构等。如果艺术主题一定要在叙事中才能得到确认,那么,叙事就需要母题、意象、题材以及结构等基本要素才完成。即艺术母题、意象、题材等在一定的图式结构中才构成叙事。换句话说,叙事是母题、意象、题材在某个逻辑展开中表述已经发生事件的独立结构,有了这个“独立结构”主题才能被清晰地揭示出来。由此看来,艺术主题与叙事是密不可分地存在于同一图式结构中的两个相关联的逻辑主体,一些没被显示的主题却会被暗示或隐喻的“空白”由观者进行补充或阐释,使“已经发生事件”的叙事趋于完整,这便是主题学、母题学所要从事的研究工作。李唐《采薇图》作品中两个人物形象是确定的,分别为伯夷、叔齐,图中石壁上著款有“河阳李唐画伯夷、叔齐”。背景“首阳山”则基本上是用山水图式暗示出来的特殊语境,因为这里的“山水”图式没有任何特质可以被认为是“首阳山”的地貌,但是可以通过观者补充完成它指涉“首阳山”这个特殊的“山水”语境,这补充的依据是提款的内容和图像中出现的挖掘工具和藤编篓,藤编篓里还有类似蕨菜叶(野薇菜)等母题元素,暗示着画中人物处在特殊的“山水”语境中,这既是《采薇图》绘画作品的图式结构与母题结构,同时也显示了《采薇图》主题的叙事结构。图画中伯夷、叔齐二入席地对坐,目光交流,似有对语,这也可以看作是《采薇图》中“情节”细化的一个母题性结构。但是这里的山水语境只有在确定了人物身份以及相关母题的出现时,“特殊语境”才可能产生明确的母题意象,否则这里的山水图式与中国传统山水画几乎没有区别,所以我们说它是暗示性的,需要观者补充或者阐释者去阐释才会有清楚的叙事逻辑结构。当然,这里还有两个母题是作为观者补充的重要细节元素,就是画中出现的类似于新石器时期水平的挖掘工具和藤编篓,它直接暗示伯夷、齐叔二人“采薇”这个情节,这个细节化的“情节”观者还可以无限补充,可以看作是绘画视觉叙事的细节化母题,也是暗示“山水”为首阳山的细节母题。一幅绘画作品的主题有着多个母题连接并存有其无限细节化的可能,这便是主题与叙事的同一基本结构。我们也可说这是绘画艺术主题以视觉方式叙事的主要特征,但这些母题、意象在图式结构中不是任何可以返回的时间动态元素,而是在结构中处于“静止”状态的,于是“静止”状态的母题、意象在结构中就有了“空白”(某种意义上与山水画的空白类似),就是说绘画作品的视觉叙事还需要观者的补充或阐释者的阐释,如同我们阐释山水画的“空白”一样,因为“在各种事物之间存在着实际上可以想象的细节的无限连续体,它们通常没有表达出来,但却‘可能’表达出来”[4]12。绘画作品中所谓的“通常没有表达出来”的是绘画艺术特性决定的,受制于绘画的“空间”因素,它们不同于“一本连环画或一部电影,都能毫不费力地转向接近长镜头并返回来”[4]12。这里就涉及我们通常说的“空间艺术”与“时间艺术”差异问题(中国长卷绘画图式另作别论)。《采薇图》需要通过对“图像”中人物(二者之间的关系)、首阳山(实际需要经验补充完成的)、藤编篓和简陋的挖掘工具等母题(实际已经成为意象),并借助“已经发生事件”的文本或传说来帮助完成叙事,从而使观者真正理解《采薇图》的主题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