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大学机构用户,欢迎您!
从伦理学的角度来看,教育政策伦理主要解决“什么样的教育政策是好的或是公正的”。对于“什么是好的或公正的”判断与选择即涉及到教育政策伦理观的基本取向问题。立足于不同伦理学流派,教育政策伦理主要表现为四种基本取向:即纯粹的社会共同善优先取向,纯粹的个体权利优先取向,社会共同善优先兼顾个体权利取向和个体权利优先兼顾社会共同善的取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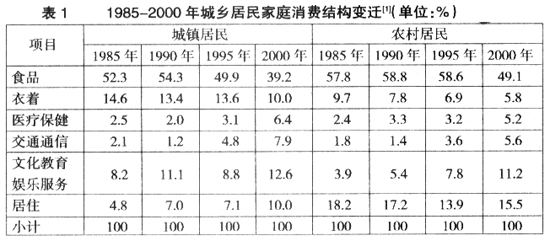 其次,在当前社会转型时期,社会利益结构日趋多元化,各利益群体政策参与的愿望不断高涨,对教育政策的回应日益增强,这就迫切需要从多方面对教育政策中的伦理价值取向进行审视与选择,以使教育政策获得最大可能多数人的支持与拥护。改革是一场利益的重组与再分配。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与深化,诸多社会利益主体日益昭显,在教育领域中亦如此。不同社会群体的教育利益需求是不同的,他们都试图通过各种手段与方式为自身或本阶层争取更多的利益。这明显地表现为,当前几乎每一项重大教育政策的出台与实施都会激起不同的回应声音。这种回应声音的不统一,一方面表明了社会大众对教育机会与资源需求的异质性;另一方面更表明了教育政策事关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在人们的利益意识与利益需求逐步增强的时代背景下,人们试图通过各种媒体与途径表达意见,以争取更多的利益。因此,面对当前社会大众对教育政策日益增强的回应状况,就更迫切地要求政府部门在制订与实施教育政策的过程中从多个方面考虑这种回应,深入思考其制订与实施的教育政策中所隐含的伦理价值观念,以使教育政策获得最大可能多数人的支持与拥护。 再次,和谐社会的提出与教育差距的不断拉大,迫切需要对教育政策的伦理价值基础进行重新思考与定位。改革开放以来,以“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为价值取向的社会改革极大地释放了人们的活动潜力,直接促进了我国经济与社会各项事业的持续高速增长。改革开放20多年来,经济建设一直是政府工作的中心,但是过分地强调经济建设,也使得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发生了断裂。改革开放初期,在“做大蛋糕”的改革模式下,人们的生产积极性与主体性被极大调动起来,虽然受益程度不同,然而社会大众普遍受益。但是“在90年代,由于资源配置机制的变化,社会中的一些人迅速暴富起来,而原来在改革初期得到一些利益的边缘和弱势群体却日益成为改革代价的承担者”,[2]这尤其明显地体现在社会成员的贫富差距上。在教育领域则表现为严峻的教育差距现状。如表2所示,1995年,东、西部农村居民教育支出之比是3.71倍,东、西部城镇居民教育支出之比是1.44倍;而到了2002年,东西部农村与城镇居民人均教育支出的差距则分别上升为3.88倍和1.97倍;而同期,东西部同一地区城乡居民的教育支出之比则分别为2.97倍和5.80倍。由此可见,教育领域内的差距现状在日益恶化。在一定意义上,教育政策的“公共性”要求政府部门在分配教育资源时,其首要的职能是保证每个社会成员“平等”地享受社会教育资源。但是现实中不断拉大的教育差距却无情地粉碎了教育政策应该具备的“平等性”。虽然“同在蓝天下”,但有的学生上学难,无钱上学;而有的学生却是上贵族学校,忙着留学。
其次,在当前社会转型时期,社会利益结构日趋多元化,各利益群体政策参与的愿望不断高涨,对教育政策的回应日益增强,这就迫切需要从多方面对教育政策中的伦理价值取向进行审视与选择,以使教育政策获得最大可能多数人的支持与拥护。改革是一场利益的重组与再分配。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与深化,诸多社会利益主体日益昭显,在教育领域中亦如此。不同社会群体的教育利益需求是不同的,他们都试图通过各种手段与方式为自身或本阶层争取更多的利益。这明显地表现为,当前几乎每一项重大教育政策的出台与实施都会激起不同的回应声音。这种回应声音的不统一,一方面表明了社会大众对教育机会与资源需求的异质性;另一方面更表明了教育政策事关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在人们的利益意识与利益需求逐步增强的时代背景下,人们试图通过各种媒体与途径表达意见,以争取更多的利益。因此,面对当前社会大众对教育政策日益增强的回应状况,就更迫切地要求政府部门在制订与实施教育政策的过程中从多个方面考虑这种回应,深入思考其制订与实施的教育政策中所隐含的伦理价值观念,以使教育政策获得最大可能多数人的支持与拥护。 再次,和谐社会的提出与教育差距的不断拉大,迫切需要对教育政策的伦理价值基础进行重新思考与定位。改革开放以来,以“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为价值取向的社会改革极大地释放了人们的活动潜力,直接促进了我国经济与社会各项事业的持续高速增长。改革开放20多年来,经济建设一直是政府工作的中心,但是过分地强调经济建设,也使得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发生了断裂。改革开放初期,在“做大蛋糕”的改革模式下,人们的生产积极性与主体性被极大调动起来,虽然受益程度不同,然而社会大众普遍受益。但是“在90年代,由于资源配置机制的变化,社会中的一些人迅速暴富起来,而原来在改革初期得到一些利益的边缘和弱势群体却日益成为改革代价的承担者”,[2]这尤其明显地体现在社会成员的贫富差距上。在教育领域则表现为严峻的教育差距现状。如表2所示,1995年,东、西部农村居民教育支出之比是3.71倍,东、西部城镇居民教育支出之比是1.44倍;而到了2002年,东西部农村与城镇居民人均教育支出的差距则分别上升为3.88倍和1.97倍;而同期,东西部同一地区城乡居民的教育支出之比则分别为2.97倍和5.80倍。由此可见,教育领域内的差距现状在日益恶化。在一定意义上,教育政策的“公共性”要求政府部门在分配教育资源时,其首要的职能是保证每个社会成员“平等”地享受社会教育资源。但是现实中不断拉大的教育差距却无情地粉碎了教育政策应该具备的“平等性”。虽然“同在蓝天下”,但有的学生上学难,无钱上学;而有的学生却是上贵族学校,忙着留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