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大学机构用户,欢迎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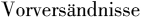 )概念”(95)。海德格尔从“作为”(Als)结构入手论述“前理解”,他把“作为”看成是“理解的先天存在论机制”(96)。比如当我们在问某个对象是什么时,我们往往已经把对象“作为”某物来称呼或把握了。所以海氏说,“解释并不是要对理解的东西有所认识,而是把理解中所筹划的可能性加以整理。理解中展开的东西,即被理解的东西,总已经是这样可达到的,即在它身上可以明确地提出它的‘作为什么’(als was)。这种‘作为’构成了某种被理解东西的明确性的结构;‘作为’构成解释。”(97)他进而反复指出,“这种解释一向奠基在一种先有(Vorhabe,亦译“前有”)之中”,“解释向来奠基于先见(Vorsicht,亦译“前识”)之中,这种先见从某种可解释状态出发对先有中所获得的东西进行‘切割’。保持在先有中的并‘先见地’被瞄准了的被理解的东西通过解释而成为可把握的。”(98)这里,先有、先见,还有先(前)把握等一系列概念都是海氏“前理解”的派生概念,或者从属于“前理解”这个总概念。有时这些概念在使用时可以交替互用。海德格尔进而确定无误地强调,“解释从来不是对先行给定的东西所作的无前提的把握。如果按照正确的本文解释的意义,解释的特殊具体化固然喜欢援引‘有典可稽’(dasteht)的东西,然而最先的‘有典可稽’的东西只不过是解释者的不言自明的无可争议的先入之见(Vormeinung)。任何解释工作之初都必然有这种先入之见,作为随着解释就已经‘设定了的’东西是先行给定了的,这就是说,是在先有、先见、先把握中先行给定了的。”(99)海德格尔的上述思想,显然与传统阐释学针锋相对。施莱尔马赫、狄尔泰的传统阐释学把目标设定为寻求历史文本及其作者的原初意义,就必然要排除解释者的任何先入之见,消除解释者的一切误解,不允许“前理解”作为解释活动的前提条件。海德格尔对解释前提的上述发现和设置,的确是对传统阐释学的重大变革。 伽达默尔本体论阐释学直接继承、发展了海德格尔有关前理解的一系列重要概念和思想。他首先批判了传统阐释学、特别是力图“消除一切前见这一启蒙运动的总要求”。如施莱尔马赫曾把阐释学定义为“避免误解的技艺”,他强调说,“我们也可将其全部任务以一种否定方式表达出来:避免每一误解”,显而易见,他的阐释学的目标就是要消除前见、避免误解、寻觅“原义”。(100)伽达默尔认为在理解中前见(Vorurteil)的存在是无法否定、也无须克服和消除的,那种“消除一切前见”的主张本身就是一种前见。与此同时,他旗帜鲜明地肯定前见在理解中的合理性、合法性,强调“如果我们想正确地对待人类的有限的历史的存在方式,那么我们就必须为前见概念根本恢复名誉,并承认有合理的前见存在”(101)。“合理的前见”成为伽达默尔阐释学的基本前提和标识性概念。“前见”于是成为理解和解释的基础。这一点对于阐释学意义观的现代转型至关重要。由此,前见、前理解不但不像传统阐释学认为的那样是理解活动需要克服、消除的东西,反而成为一切理解无法摆脱的必要前提和出发点。任何理解活动,理解者总是不可避免地带着某种自己的前理解、前见进入理解的。因此,“一切诠释学条件中最首要的条件总是前理解,这种前理解来自于与同一事情相关联的存在(im Zu-tun-ha-ben mit der gleichen Sache)。正是这种前理解规定了什么可以作为统一的意义被实现,并从而规定了对完全性的前把握的应用。”(102)由于本体论阐释学目标的这一根本改变,传统阐释学将一切前见当作误解而要求绝对排除的观点也转变为肯定前见(哪怕是成见、偏见)的合理性,并名正言顺地成为一切理解活动的必然和必要前提。 关于前见(Vorurteil)的含义,伽达默尔曾说,“实际上前见就是一种判断,它是在一切对于事情具有决定性作用的要素被最后考察之前被给予的。”(103)在他看来,前见(如前判断、前假设等)不仅在理解的开始阶段发生作用,而且延伸到整个理解过程中,是在对被理解对象理解的过程中不断被给予,并参与理解、发生作用的。因而“只有理解者顺利地带进了他自己的假设,理解才是可能的。解释的生产性的贡献永远属于理解的内容本身”(104)。后面这句话实际上还提出了前见的参与促成了理解的生产性即创造性的问题。 与传统阐释学把解释归结为寻找、还原文本和作者的原初意义不同,伽达默尔突出了解释者解释的创造性,他说,“解释在某种特定的意义上就是再创造(Nachschaffen),但是这种再创造所根据的不是一个先行的创造行为,而是所创造的作品的形象(Figur),解释者按照他在其中所发现的意义使这形象达到表现。”(105)按笔者理解,这里“先行的创造行为”,是指文本作者的创造行为,它不应成为解释者解读、再创造的依据;作者创造行为所创造的文本中的形象才是解释者理解的依据或出发点;但是,这种文本提供的形象不能看成是已经完成、固定不变的现成品,而是在解释者再创造的过程中其意义被不断发现、更新,形象才一步步得到展示和表现的。显然,在伽氏那里,文本的意义主要不能到作者创造活动、行为中去寻觅,而只有通过读者、解释者在其前见指引下的不断再创造,文本(作品)的形象及其意义才能逐步得到展示和表现。由此可见,前见不仅在限制和在某种程度上规定了读者、解释者理解的方向、范围、重点,使理解带有某种倾向性,而且,有助于激发理解的生产性和创造性,这正是造成解释的多义性的根源。这是伽氏哲学阐释学不同于并超越传统阐释学的一个根本点,是对海德格尔本体论阐释学思路的直接接续。
)概念”(95)。海德格尔从“作为”(Als)结构入手论述“前理解”,他把“作为”看成是“理解的先天存在论机制”(96)。比如当我们在问某个对象是什么时,我们往往已经把对象“作为”某物来称呼或把握了。所以海氏说,“解释并不是要对理解的东西有所认识,而是把理解中所筹划的可能性加以整理。理解中展开的东西,即被理解的东西,总已经是这样可达到的,即在它身上可以明确地提出它的‘作为什么’(als was)。这种‘作为’构成了某种被理解东西的明确性的结构;‘作为’构成解释。”(97)他进而反复指出,“这种解释一向奠基在一种先有(Vorhabe,亦译“前有”)之中”,“解释向来奠基于先见(Vorsicht,亦译“前识”)之中,这种先见从某种可解释状态出发对先有中所获得的东西进行‘切割’。保持在先有中的并‘先见地’被瞄准了的被理解的东西通过解释而成为可把握的。”(98)这里,先有、先见,还有先(前)把握等一系列概念都是海氏“前理解”的派生概念,或者从属于“前理解”这个总概念。有时这些概念在使用时可以交替互用。海德格尔进而确定无误地强调,“解释从来不是对先行给定的东西所作的无前提的把握。如果按照正确的本文解释的意义,解释的特殊具体化固然喜欢援引‘有典可稽’(dasteht)的东西,然而最先的‘有典可稽’的东西只不过是解释者的不言自明的无可争议的先入之见(Vormeinung)。任何解释工作之初都必然有这种先入之见,作为随着解释就已经‘设定了的’东西是先行给定了的,这就是说,是在先有、先见、先把握中先行给定了的。”(99)海德格尔的上述思想,显然与传统阐释学针锋相对。施莱尔马赫、狄尔泰的传统阐释学把目标设定为寻求历史文本及其作者的原初意义,就必然要排除解释者的任何先入之见,消除解释者的一切误解,不允许“前理解”作为解释活动的前提条件。海德格尔对解释前提的上述发现和设置,的确是对传统阐释学的重大变革。 伽达默尔本体论阐释学直接继承、发展了海德格尔有关前理解的一系列重要概念和思想。他首先批判了传统阐释学、特别是力图“消除一切前见这一启蒙运动的总要求”。如施莱尔马赫曾把阐释学定义为“避免误解的技艺”,他强调说,“我们也可将其全部任务以一种否定方式表达出来:避免每一误解”,显而易见,他的阐释学的目标就是要消除前见、避免误解、寻觅“原义”。(100)伽达默尔认为在理解中前见(Vorurteil)的存在是无法否定、也无须克服和消除的,那种“消除一切前见”的主张本身就是一种前见。与此同时,他旗帜鲜明地肯定前见在理解中的合理性、合法性,强调“如果我们想正确地对待人类的有限的历史的存在方式,那么我们就必须为前见概念根本恢复名誉,并承认有合理的前见存在”(101)。“合理的前见”成为伽达默尔阐释学的基本前提和标识性概念。“前见”于是成为理解和解释的基础。这一点对于阐释学意义观的现代转型至关重要。由此,前见、前理解不但不像传统阐释学认为的那样是理解活动需要克服、消除的东西,反而成为一切理解无法摆脱的必要前提和出发点。任何理解活动,理解者总是不可避免地带着某种自己的前理解、前见进入理解的。因此,“一切诠释学条件中最首要的条件总是前理解,这种前理解来自于与同一事情相关联的存在(im Zu-tun-ha-ben mit der gleichen Sache)。正是这种前理解规定了什么可以作为统一的意义被实现,并从而规定了对完全性的前把握的应用。”(102)由于本体论阐释学目标的这一根本改变,传统阐释学将一切前见当作误解而要求绝对排除的观点也转变为肯定前见(哪怕是成见、偏见)的合理性,并名正言顺地成为一切理解活动的必然和必要前提。 关于前见(Vorurteil)的含义,伽达默尔曾说,“实际上前见就是一种判断,它是在一切对于事情具有决定性作用的要素被最后考察之前被给予的。”(103)在他看来,前见(如前判断、前假设等)不仅在理解的开始阶段发生作用,而且延伸到整个理解过程中,是在对被理解对象理解的过程中不断被给予,并参与理解、发生作用的。因而“只有理解者顺利地带进了他自己的假设,理解才是可能的。解释的生产性的贡献永远属于理解的内容本身”(104)。后面这句话实际上还提出了前见的参与促成了理解的生产性即创造性的问题。 与传统阐释学把解释归结为寻找、还原文本和作者的原初意义不同,伽达默尔突出了解释者解释的创造性,他说,“解释在某种特定的意义上就是再创造(Nachschaffen),但是这种再创造所根据的不是一个先行的创造行为,而是所创造的作品的形象(Figur),解释者按照他在其中所发现的意义使这形象达到表现。”(105)按笔者理解,这里“先行的创造行为”,是指文本作者的创造行为,它不应成为解释者解读、再创造的依据;作者创造行为所创造的文本中的形象才是解释者理解的依据或出发点;但是,这种文本提供的形象不能看成是已经完成、固定不变的现成品,而是在解释者再创造的过程中其意义被不断发现、更新,形象才一步步得到展示和表现的。显然,在伽氏那里,文本的意义主要不能到作者创造活动、行为中去寻觅,而只有通过读者、解释者在其前见指引下的不断再创造,文本(作品)的形象及其意义才能逐步得到展示和表现。由此可见,前见不仅在限制和在某种程度上规定了读者、解释者理解的方向、范围、重点,使理解带有某种倾向性,而且,有助于激发理解的生产性和创造性,这正是造成解释的多义性的根源。这是伽氏哲学阐释学不同于并超越传统阐释学的一个根本点,是对海德格尔本体论阐释学思路的直接接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