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大学机构用户,欢迎您!
在20世紀高調宣揚文學“自治”的浪潮退去以後,當代的文學批評承認,文學與人類學這兩個曾經相互輕視的學科之間存在着萬宗歸一的關係。正是在這樣一種思潮的背景下,學術界不斷將一些人類學的思考引入文學研究的範疇。如果將法國文學理論家讓·貝西埃與英國人類學家阿爾弗雷德·蓋爾的理論結合起來進行閱讀,可以在他們視角迥異的理論著作中發現有一個相似的設想:人工製品或者說作品(主要是西方的藝術作品)對於其所處的現實環境具有一種行動、效力和能動性。基於兩位學者的闡述,人們得以將“藝術”的這一行動描述爲“‘意圖’向‘意識’的呈現”。但需要注意的是,在文學中意圖的呈現,與蓋爾在其研究所涉及的美學表現形式當中觀察到的有着根本的區別:後者是一種機關裝置,作品借用它實現意圖的傳遞,並在這一過程中建立一種從屬關係,實現對接受者的奴役。這樣一種意圖裝置雖然適用於經典的文藝作品,但在當代的文學和藝術中顯然已經失去了效用,讀者和觀者在這些作品面前常常感到無所適從。因此,要繼續討論這些複雜作品的意圖性,就需要在這兩個理論之外引入其他學者例如雅克·朗西耶的政治學觀點,將藝術作品的意圖及其行動描述爲一種“異見”的呈現。如此,將接受者從作品的奴役中解放出來纔成爲可能;而這一“解放”,則蘊涵着作品的政治行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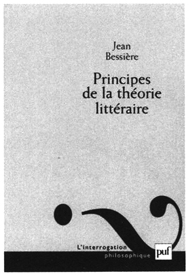 《文學理論概述》
《文學理論概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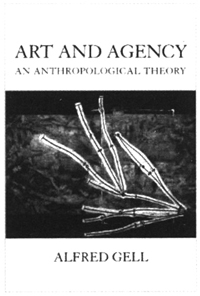 《兿術與能動性》 貝西埃十分看重文學作品中所體現出來的這對基本關係。他認爲,“乍一看,將作品即文本這一死的東西與行動等同起來,是自相矛盾的”③,然而實際上,文學對產生了它的周邊現實環境是有所行動的。④在談到作品在認知方面的屬性時,作者並沒有妄下定論,而是以提問的方式表達了自己的思考: 當我們想要確定作品的認知或象徵屬性是現實主義還是反現實主義的時候,或者當我們無力闡述或拒絕闡述這一屬性的時候,我們需要思考一個問題:對環境現有結構的複製和表現,以及對被表現物的定義範式的複製和表現,要如何纔能在對這些結構和範式無動於衷的東西面前體現出價值來?⑤ 雖然作者所提出的僅僅是一個簡單的問題而已,但他已經考慮到了該問題所有的相關指涉。 接續他的問題是:文學作品對周圍環境僅僅是複製而已嗎?因爲,在這個假設之下,作品與現實之間已毫無區別可言,脫離了前者作爲“語言的純粹產物”的這個定義。當然,有一些作品樂於承認自身與社會現實之間的關聯——它們甚至藉此找到證明其存在的合理攀附。但即便這些作品與種種象徵的、形式的、構成了現實社會的一切均值編碼系統掛起鉤來,它們也衹能部分地、遴選性地,或者說是帶有意圖地去重複這些環境的某一些要素;如果在作品中想要複製現實社會的象徵、符號和話語,衹能通過置換、變形、隱避,通過一種特殊的眼光、一面棱鏡、一種距離,纔能得以實現。 然而,這一文學的,當然也是所有美學實踐活動的根本的“異質性”(altérité),在西方藝術史尤其是文學藝術史中常常被掩藏起來:整個古典主義時期——即米歇爾·福柯(M.Foucault,1926-1984)所謂的“再現的認識論”時期,在其形成(自14—15世紀開始)、傳播和發展過程中,試圖發展出一種完全複製環境的假象,以此建立一個以人類爲中心的開化世界的副本。19世紀以後,哲學和文學批評從德國浪漫主義如施勒格爾(K.W.F.Schlegel,1772-1829)、謝林(F.W.J.V.Schelling,1775-1854)、諾瓦利斯(Novalis,1772-1801)、霍夫曼(E.T.W.Hoffman,1776-1822)等人開始,及至其後所有的形式主義者,再到“語言學轉向”,發展出一部洋洋灑灑的“寫作的神話”(mythologis de l'écriture),將作品定義爲“人工製品”(artéfact),一種表意的結構,一種自我指涉的東西。
《兿術與能動性》 貝西埃十分看重文學作品中所體現出來的這對基本關係。他認爲,“乍一看,將作品即文本這一死的東西與行動等同起來,是自相矛盾的”③,然而實際上,文學對產生了它的周邊現實環境是有所行動的。④在談到作品在認知方面的屬性時,作者並沒有妄下定論,而是以提問的方式表達了自己的思考: 當我們想要確定作品的認知或象徵屬性是現實主義還是反現實主義的時候,或者當我們無力闡述或拒絕闡述這一屬性的時候,我們需要思考一個問題:對環境現有結構的複製和表現,以及對被表現物的定義範式的複製和表現,要如何纔能在對這些結構和範式無動於衷的東西面前體現出價值來?⑤ 雖然作者所提出的僅僅是一個簡單的問題而已,但他已經考慮到了該問題所有的相關指涉。 接續他的問題是:文學作品對周圍環境僅僅是複製而已嗎?因爲,在這個假設之下,作品與現實之間已毫無區別可言,脫離了前者作爲“語言的純粹產物”的這個定義。當然,有一些作品樂於承認自身與社會現實之間的關聯——它們甚至藉此找到證明其存在的合理攀附。但即便這些作品與種種象徵的、形式的、構成了現實社會的一切均值編碼系統掛起鉤來,它們也衹能部分地、遴選性地,或者說是帶有意圖地去重複這些環境的某一些要素;如果在作品中想要複製現實社會的象徵、符號和話語,衹能通過置換、變形、隱避,通過一種特殊的眼光、一面棱鏡、一種距離,纔能得以實現。 然而,這一文學的,當然也是所有美學實踐活動的根本的“異質性”(altérité),在西方藝術史尤其是文學藝術史中常常被掩藏起來:整個古典主義時期——即米歇爾·福柯(M.Foucault,1926-1984)所謂的“再現的認識論”時期,在其形成(自14—15世紀開始)、傳播和發展過程中,試圖發展出一種完全複製環境的假象,以此建立一個以人類爲中心的開化世界的副本。19世紀以後,哲學和文學批評從德國浪漫主義如施勒格爾(K.W.F.Schlegel,1772-1829)、謝林(F.W.J.V.Schelling,1775-1854)、諾瓦利斯(Novalis,1772-1801)、霍夫曼(E.T.W.Hoffman,1776-1822)等人開始,及至其後所有的形式主義者,再到“語言學轉向”,發展出一部洋洋灑灑的“寫作的神話”(mythologis de l'écriture),將作品定義爲“人工製品”(artéfact),一種表意的結構,一種自我指涉的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