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现代诗歌相比,古希腊诗歌至少有两点不同:其一,古希腊的传统诗歌总体而言都是合唱诗歌,而不是个人私性的写作;其次,古希腊的合唱诗歌均是为公开表演而作——无论是人数相对较少的会饮场合,还是整个城邦的宗法节日(Kurke "Introduction"),而后者尤其体现了希腊传统贵族政制的习俗和礼法(Bowra 2)。这就意味着,古希腊诗歌和城邦之间具有活生生的关联,具有严肃的政制性质。所以,柏拉图才会在《法律篇》(Laws)中写道:“我们说一个人‘没有受过教育’,是指一个没有受过合唱训练的人”(654b)。被昆体良誉为希腊“抒情诗人之首”的品达(Pindar),其为竞技比赛胜利而写的凯歌(ode),无论诗之洵美,抑或政治伦常之传达,均可称之为这种合唱诗歌的巅峰。 实际上,品达书写凯歌,这一行为方式和他的凯歌本身,便已彰显了诗人在传统政治生活中的位置。不过,我们唯有进入凯歌的具体言辞,方能深究其中三昧。尤其是,品达在凯歌中经常以第一人称发言,只是这个第一人称的“我”,究竟是指品达本人,还是诗歌形象,或者合唱歌队,学界尚有各种争论。晚近20余年,品达研究的核心问题是凯歌的表演:即,品达写下的诗行在当时的历史情境下如何进行具体的表演,这尤其牵涉到凯歌中第一人称的“我”。①这本是人类学研究方法在古典研究和文学研究领域的反应,不过,却在另外一个意义上说明了凯歌与共同体生活方式之间的关系,恰也验证了柏拉图关于合唱训练的说法:合唱直接关涉城邦教育的政治问题。②正是由于凯歌的表演,凯歌才最终实现肉身,并因此而成为一种政治生活方式。这个问题的关键要点或许在于:凯歌中频频出现的第一人称功能何在。 关于凯歌中的这个“我”究竟指谁,历来众说纷纭,阿勒西奥(G.B.D' Alessio)批评说,“在凯歌表演,或者诗歌的创造中强行区分出一个言说者的角色,这不但不可能,恐怕也无益处可言”(127)。所以,更多的学者尝试回到凯歌的具体文本和语境,列夫科沃茨(M.R.Lefkowitz)在论证凯歌单独表演时,给出的一个说法值得留意:品达使用这些第一人称来表述一种“特定的角色”(professional persona),所以,他假定这种“诗人的我”在凯歌里有一种统一的戏剧特征(79)。与此类似,斯纳特(W.J.Slater)认为,第一人称是“一种品达、歌队和歌队长模糊的综合”(89),是一种“综合性的”我。利多夫(J.B.Lidov)将“我”看作是“一种表达方式,而不是所要表达的东西”,那它就会像其他方式一样,“根据具体情景而发生相应的变化”(79)。所以,沙利文(Shirley Sullivan)称这个“我”是一个“虚构的我”(Fictive I),强调“我”在具体凯歌表演中的戏剧特征,倾向于将“我”理解为表演中的一个戏剧“角色”(dramatic persona),同时,又是一个体现凯歌具体情境的“角色”。③ 借助这番梳理,我们不难看出,将“我”或者第一人称抽象为某个诗学问题,无助于我们理解品达和他悉心写下的凯歌,我们更应回到凯歌的文本本身——不过,所谓“文本”,尚有两个更为宽泛的理解:凯歌所在政治场景、品达置身其中的希腊诗歌传统。注目于这三重文本,我们方能明白,诗人和诗歌在传统政治生活中的位置。下文以第八首皮托凯歌中的第一人称表达为例(品达 行60-80),略作分析。公元前446年,埃吉纳人的年轻人阿里斯托墨涅斯(Aristomenes)在皮托竞技会上获得摔跤比赛的冠军,品达为他写下这首凯歌在其母邦埃吉纳传唱数年。根据抄件的记载,第八首皮托凯歌(the eighth Pythian)所赞颂的胜利,是第35届皮托竞技会上的摔跤比赛,根据确切的时间记载,这是品达的最后一首凯歌,也可以视为希腊诗歌史上的最后一首凯歌。因为在公元前5世纪,诗歌和音乐的品味急剧转变,戏剧开始占据城邦的核心位置,同时又出现新的合唱歌方式;竞技会丧失了它们本来具有的希腊文化中心地位。Finley认为理性的思考和书写方式,最终取代了合唱诗的统治地位,衰落的不仅仅是凯歌,而且是整个抒情诗的传统。④作为凯歌的天鹅绝唱,作为对古希腊贵族传统竞技精神最后的颂扬,这首凯歌无比清晰地再现了希腊传统诗歌的思考。 第八首皮托凯歌的第二转题部分(行61-80),第一个词语是“你”

,这是

(你)的多里斯方言写法,这似乎表明,这部分的重点并不在于“我”。但是,“你”的出现,恰恰表明“我”对一位在场者的称呼,意味着一次对话的展开,这无疑是凯歌中“我”对一个在场者的直接描述——凯歌中“我”的戏剧角色,其含义便在于此。不过,复杂之处在于,这一部分短短20行,“你”的称呼却依次历经了三重变化:太阳神、阿里斯托墨涅斯之父克塞纳克斯和阿里斯托墨涅斯本人。其实,此处三重对话恰恰对应了诗人的政治位置。 一、神与诗人 这首凯歌开篇即向安宁女神吁请(行1),此处同样向另一位神明吁请,即远射之神阿波罗(行61)。远射之神是对太阳神阿波罗的习惯称呼,比如《伊利亚特》中第一次提到阿波罗称其为“勒托和宙斯之子”,随后便称其为“远射之神”,而在整个第一卷中也都强调阿波罗这一特征(荷马 行14;96;370等);不过,我们更需注意的是,阿波罗的先知和祭司克律塞斯“手中的金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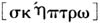
举着远射神阿波罗的花冠”(荷马 行14),太阳神与诗人的权杖息息相关。缪斯也赠给赫西俄德同样的权杖(赫西俄德 行30-31),所以,当品达在凯歌中称太阳神为远射之神的时候,暗指了诗人手执“权杖”,与神(缪斯和阿波罗)之间关系密切。借这个称呼,“我”凸显了自己与阿波罗之间的关联。
 ,这是
,这是 (你)的多里斯方言写法,这似乎表明,这部分的重点并不在于“我”。但是,“你”的出现,恰恰表明“我”对一位在场者的称呼,意味着一次对话的展开,这无疑是凯歌中“我”对一个在场者的直接描述——凯歌中“我”的戏剧角色,其含义便在于此。不过,复杂之处在于,这一部分短短20行,“你”的称呼却依次历经了三重变化:太阳神、阿里斯托墨涅斯之父克塞纳克斯和阿里斯托墨涅斯本人。其实,此处三重对话恰恰对应了诗人的政治位置。 一、神与诗人 这首凯歌开篇即向安宁女神吁请(行1),此处同样向另一位神明吁请,即远射之神阿波罗(行61)。远射之神是对太阳神阿波罗的习惯称呼,比如《伊利亚特》中第一次提到阿波罗称其为“勒托和宙斯之子”,随后便称其为“远射之神”,而在整个第一卷中也都强调阿波罗这一特征(荷马 行14;96;370等);不过,我们更需注意的是,阿波罗的先知和祭司克律塞斯“手中的金杖
(你)的多里斯方言写法,这似乎表明,这部分的重点并不在于“我”。但是,“你”的出现,恰恰表明“我”对一位在场者的称呼,意味着一次对话的展开,这无疑是凯歌中“我”对一个在场者的直接描述——凯歌中“我”的戏剧角色,其含义便在于此。不过,复杂之处在于,这一部分短短20行,“你”的称呼却依次历经了三重变化:太阳神、阿里斯托墨涅斯之父克塞纳克斯和阿里斯托墨涅斯本人。其实,此处三重对话恰恰对应了诗人的政治位置。 一、神与诗人 这首凯歌开篇即向安宁女神吁请(行1),此处同样向另一位神明吁请,即远射之神阿波罗(行61)。远射之神是对太阳神阿波罗的习惯称呼,比如《伊利亚特》中第一次提到阿波罗称其为“勒托和宙斯之子”,随后便称其为“远射之神”,而在整个第一卷中也都强调阿波罗这一特征(荷马 行14;96;370等);不过,我们更需注意的是,阿波罗的先知和祭司克律塞斯“手中的金杖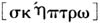 举着远射神阿波罗的花冠”(荷马 行14),太阳神与诗人的权杖息息相关。缪斯也赠给赫西俄德同样的权杖(赫西俄德 行30-31),所以,当品达在凯歌中称太阳神为远射之神的时候,暗指了诗人手执“权杖”,与神(缪斯和阿波罗)之间关系密切。借这个称呼,“我”凸显了自己与阿波罗之间的关联。
举着远射神阿波罗的花冠”(荷马 行14),太阳神与诗人的权杖息息相关。缪斯也赠给赫西俄德同样的权杖(赫西俄德 行30-31),所以,当品达在凯歌中称太阳神为远射之神的时候,暗指了诗人手执“权杖”,与神(缪斯和阿波罗)之间关系密切。借这个称呼,“我”凸显了自己与阿波罗之间的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