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大学机构用户,欢迎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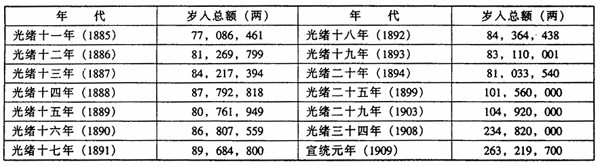 财政收入规模的大小和增长速度的快慢不仅受政府财经政策的影响,更主要地是受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经济发展水平及蕴含于其中的技术进步对财政收入规模的影响是根本性的,清代财政收入规模正是在当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基础上不断发展的。 清初,由于战争的频繁和灾荒的破坏,社会经济残破凋敝,百姓生计困窘艰难。为了恢复经济,清政府不得不减免赋税,与民休息。据史料记载,仅康熙在位的前四十四年,蠲免钱粮即达9000万两有奇(注:《清圣祖实录》卷二二三。)。乾隆时的蠲免规模更是远胜前朝。乾隆十年(1745),朝廷决定于次年起分三年轮免各省额征银数,此次共计免征赋银2824万余两(注:《清史稿》卷一二五,食货六。)。此后又分别于乾隆三十五年(1770)、四十三年(1778)、五十五年(1790)普免全国钱粮(注:《清高宗实录》卷八五○,卷一○二五,卷一三五○、卷一四四一。)。依据当时的地丁收入水平粗略统计,乾隆一朝仅普免赋银就有一亿两以上。蠲免之外,清政府还要赈济灾荒,疏浚河工,用度也颇繁。恢复经济的代价是非常大的,清政府为此损失了为数不菲的财政收入,从而影响了收入规模的扩大。 商品经济在前清有了一定发展,但由于统治者厉行“重农抑商”政策,工商业发展受到限制,对外贸易也被长期遏制。因此,清政府的财政收入只能以田赋为主体,而“永不加赋”、“摊丁入亩”等改革又将田赋征收定额化,这就决定了前清的财政收入不可能有快速发展,而是长期徘徊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之上。 鸦片战争后,中国经济发生了深刻变化。随着外国的商品倾销和资本输出,原来以个体生产为基础的自然经济逐渐走向解体,已有的资本主义萌芽在外国资本的影响和刺激下进行了技术改造,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得以产生并有了初步发展。清政府为“自强”、“求富”,在政策上对工商业发展逐渐由抑禁转为认可和鼓励,对于外国先进技术亦主张积极引进。洋务运动期间及以后,西方科学著作不断被翻译介绍到中国,实用技术也伴随着外资的侵入及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源源而来,从而促进了近代工业经济的发展,提高了经济效益。就冶铁工业而言,光绪二十六年(1900),全国生铁产量25890吨,三十一年(1905)为32313吨,宣统二年(1910)骤增至119396吨(注:杜石然等编:《中国科学技术史稿》下册,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283页。)。这一巨大成就无疑归功于近代冶铁技术的传入与应用。美国学者费维恺认为,“近代前的”经济扩张是一种“低度开发”,是在落后状态下的成长;“近代性的”经济成长则是由于科技不断进步而形成的(注:(美)费维恺:《清代经济史与世界经济史》,载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明清档案与历史研究》上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93-394页。)。这一观点比较中肯,也适用于前清与晚清的经济发展状况。晚清的经济发展与技术进步使财政收入因财源扩展而增加,这一点是前清无可比拟的,其财政收入规模也达到了后者难以想象的扩张程度。
财政收入规模的大小和增长速度的快慢不仅受政府财经政策的影响,更主要地是受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经济发展水平及蕴含于其中的技术进步对财政收入规模的影响是根本性的,清代财政收入规模正是在当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基础上不断发展的。 清初,由于战争的频繁和灾荒的破坏,社会经济残破凋敝,百姓生计困窘艰难。为了恢复经济,清政府不得不减免赋税,与民休息。据史料记载,仅康熙在位的前四十四年,蠲免钱粮即达9000万两有奇(注:《清圣祖实录》卷二二三。)。乾隆时的蠲免规模更是远胜前朝。乾隆十年(1745),朝廷决定于次年起分三年轮免各省额征银数,此次共计免征赋银2824万余两(注:《清史稿》卷一二五,食货六。)。此后又分别于乾隆三十五年(1770)、四十三年(1778)、五十五年(1790)普免全国钱粮(注:《清高宗实录》卷八五○,卷一○二五,卷一三五○、卷一四四一。)。依据当时的地丁收入水平粗略统计,乾隆一朝仅普免赋银就有一亿两以上。蠲免之外,清政府还要赈济灾荒,疏浚河工,用度也颇繁。恢复经济的代价是非常大的,清政府为此损失了为数不菲的财政收入,从而影响了收入规模的扩大。 商品经济在前清有了一定发展,但由于统治者厉行“重农抑商”政策,工商业发展受到限制,对外贸易也被长期遏制。因此,清政府的财政收入只能以田赋为主体,而“永不加赋”、“摊丁入亩”等改革又将田赋征收定额化,这就决定了前清的财政收入不可能有快速发展,而是长期徘徊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之上。 鸦片战争后,中国经济发生了深刻变化。随着外国的商品倾销和资本输出,原来以个体生产为基础的自然经济逐渐走向解体,已有的资本主义萌芽在外国资本的影响和刺激下进行了技术改造,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得以产生并有了初步发展。清政府为“自强”、“求富”,在政策上对工商业发展逐渐由抑禁转为认可和鼓励,对于外国先进技术亦主张积极引进。洋务运动期间及以后,西方科学著作不断被翻译介绍到中国,实用技术也伴随着外资的侵入及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源源而来,从而促进了近代工业经济的发展,提高了经济效益。就冶铁工业而言,光绪二十六年(1900),全国生铁产量25890吨,三十一年(1905)为32313吨,宣统二年(1910)骤增至119396吨(注:杜石然等编:《中国科学技术史稿》下册,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283页。)。这一巨大成就无疑归功于近代冶铁技术的传入与应用。美国学者费维恺认为,“近代前的”经济扩张是一种“低度开发”,是在落后状态下的成长;“近代性的”经济成长则是由于科技不断进步而形成的(注:(美)费维恺:《清代经济史与世界经济史》,载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明清档案与历史研究》上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93-394页。)。这一观点比较中肯,也适用于前清与晚清的经济发展状况。晚清的经济发展与技术进步使财政收入因财源扩展而增加,这一点是前清无可比拟的,其财政收入规模也达到了后者难以想象的扩张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