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大学机构用户,欢迎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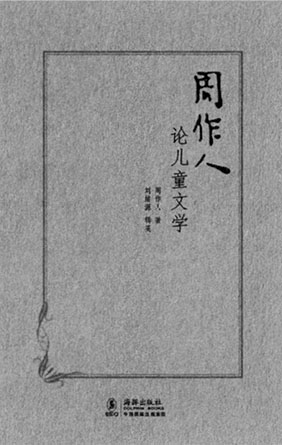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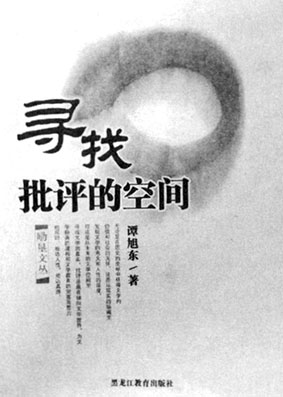 一、“迎合儿童心理”的批评标准 “迎合儿童心理”②是中国儿童文学产生以来的第一条批评标准,它的影响贯穿了中国儿童文学发展的始终。该标准有两层含义:其一,符合儿童独特的审美心理个性,富有儿童情趣。其二,照顾特定年龄阶段儿童读者的阅读理解能力和阅读趣味,能吸引儿童阅读,便于儿童理解。 前者产生于五四时期。在新文化运动“人的解放”旗帜下,周作人提出个人主义的精神生活解放思想③,推崇人的个性和个体精神生活需要,首次将儿童独特的审美趣味合理化并作为儿童文学区别于成人文学的本质特征置于极高的价值位置,以此从成人审美和道学教育中独立出一种特殊供给儿童阅读的文学——儿童文学。为维护儿童独特的精神生活需要④,将儿童从成人和传统的压抑中拯救出来,该标准强调儿童与成人审美趣味的差异,将富有儿童游戏心理特性的“无意思之意思”⑤视为最高标准。这就要求成人作家基于儿童心理创作。如郭沫若提出,儿童文学创作“必熟悉儿童心理或赤子之心未失的人,如化身而为婴儿自由地表现其情感与想象”⑥。叶圣陶倡导:“对准儿童内发的感情而为之相应,使益丰富而纯美。”⑦周作人认为创作儿童文学“非熟通儿童心理者不能试,非自具儿童心理者不能善。”⑧在构建独属于儿童的精神生活世界的倡导下,作品是否表现了纯正的儿童心理就成为判断儿童文学品质的最高标准。20世纪八九十年代班马提出的“儿童反儿童化”“原始思维”“前艺术思想”等理论即是对此标准的遥远呼应,都是通过对儿童心理的认识推进和趋近而推动了创作观念的更新。只是对儿童心理的研究不再止步于成人凝视的“自然天真”,更为科学深入且更符合时代少年特征。 此标准是特定环境下对“父为子纲”传统思想的强烈反拨,为中国儿童文学的独立发展以及独特审美风格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其结果为将儿童的童真稚趣内化提升为一种文学的审美风格,不仅以纯净、愉悦、无功利的审美特性为儿童筑造出一个独享的纯美世界,更为儿童的天性生活争取了文学的自由空间。另一方面,该审美推崇也展示了对“文以载道”“反映社会”“抒发作者情感”等传统文学价值的反叛,而推崇一种更为朝气、理想化、富有想象力的文学风格。在提倡教育功能的20世纪50年代,该标准的延续也保证了儿童文学与儿童读者的亲近性,产生了不少广受儿童欢迎的儿童文学作品。 而“照顾儿童阅读能力”的标准则得益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儿童文学作为“小学校里的文学”所具有的革新儿童教育的功能。以郑振铎为代表,将儿童文学作为尊重儿童特点的教育工具,以教育性作为儿童文学的根本特性,从而强调儿童文学与儿童阅读能力和阅读趣味的适配性。这种标准一方面强调儿童文学作为一种新式教育在思想内容上的独特与先进,要求“内容适合于儿童的年龄与智慧,情绪的发展的程序”⑨,反对“顺民或忠臣孝子的教育”⑩,且拒绝将儿童视作原人,将“神话、传说、神仙故事等”“人类的童年时代的产物”,“野蛮时代的‘成人’的出产物,全都搬给了近代的儿童去读”(11)。另一方面,强调成人对作品的改编技巧,务必契合儿童的理解能力和阅读兴趣,从而达到意义传达与接受的良好效果。郑振铎在《儿童文学的教授法》中引用了美国儿童文学理论家提出的三项原则,要点为:一、“应适宜于儿童的性情和习惯”“趣味和嗜好”;二、“所用的地名物名人名”须为特定儿童接受者所熟知;三、“新奇而不费解释的事物”“不妨尽量引用”以“扩充儿童智识范围”,“迎合他们的好奇心”(12)。可以看到,从教育工具角度出发的批评标准,是将儿童作为文本接受者来看待,以文本意义及传达的便利性和有效性作为评价儿童文学好坏的标准。它也强调儿童文学的特殊性,只是并不将其限定为对儿童生活心理的了解和再现,而是基于对儿童阅读心理和状况的把握,因时制宜迎合儿童的阅读视野,从而增加文本的亲和性,降低阅读理解难度,吸引儿童自主阅读接受,最终达到成人开发拓展儿童智识的最终目的。相比以儿童审美气质为审美境界追求的浪漫抽象,此标准更讲求实证性和技术操作性。其一,它注重对现实读者需求的客观把握,如1931年徐锡龄对不同年龄、性别儿童阅读兴趣的调研和实证研究(13)。其二,注重文本编写策略,迎合儿童兴趣,便于理解记忆,以保证教育信息被主动接收并留下印象。如20世纪30年代左翼作家华汉指出:“儿童读的东西与成人读的不同,儿童读物应该要有趣味——当然仅仅是技术上的趣味。”(14)钱杏邨、田汉、叶沉、沈起予、冯宪章、周全平等左翼作家亦提倡征求小朋友意见,了解少年趣味,并提出诸多如文字通俗浅显,多加色彩、插画,多用注音字母,多加歌曲等具体可操作的文本编织手段。
一、“迎合儿童心理”的批评标准 “迎合儿童心理”②是中国儿童文学产生以来的第一条批评标准,它的影响贯穿了中国儿童文学发展的始终。该标准有两层含义:其一,符合儿童独特的审美心理个性,富有儿童情趣。其二,照顾特定年龄阶段儿童读者的阅读理解能力和阅读趣味,能吸引儿童阅读,便于儿童理解。 前者产生于五四时期。在新文化运动“人的解放”旗帜下,周作人提出个人主义的精神生活解放思想③,推崇人的个性和个体精神生活需要,首次将儿童独特的审美趣味合理化并作为儿童文学区别于成人文学的本质特征置于极高的价值位置,以此从成人审美和道学教育中独立出一种特殊供给儿童阅读的文学——儿童文学。为维护儿童独特的精神生活需要④,将儿童从成人和传统的压抑中拯救出来,该标准强调儿童与成人审美趣味的差异,将富有儿童游戏心理特性的“无意思之意思”⑤视为最高标准。这就要求成人作家基于儿童心理创作。如郭沫若提出,儿童文学创作“必熟悉儿童心理或赤子之心未失的人,如化身而为婴儿自由地表现其情感与想象”⑥。叶圣陶倡导:“对准儿童内发的感情而为之相应,使益丰富而纯美。”⑦周作人认为创作儿童文学“非熟通儿童心理者不能试,非自具儿童心理者不能善。”⑧在构建独属于儿童的精神生活世界的倡导下,作品是否表现了纯正的儿童心理就成为判断儿童文学品质的最高标准。20世纪八九十年代班马提出的“儿童反儿童化”“原始思维”“前艺术思想”等理论即是对此标准的遥远呼应,都是通过对儿童心理的认识推进和趋近而推动了创作观念的更新。只是对儿童心理的研究不再止步于成人凝视的“自然天真”,更为科学深入且更符合时代少年特征。 此标准是特定环境下对“父为子纲”传统思想的强烈反拨,为中国儿童文学的独立发展以及独特审美风格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其结果为将儿童的童真稚趣内化提升为一种文学的审美风格,不仅以纯净、愉悦、无功利的审美特性为儿童筑造出一个独享的纯美世界,更为儿童的天性生活争取了文学的自由空间。另一方面,该审美推崇也展示了对“文以载道”“反映社会”“抒发作者情感”等传统文学价值的反叛,而推崇一种更为朝气、理想化、富有想象力的文学风格。在提倡教育功能的20世纪50年代,该标准的延续也保证了儿童文学与儿童读者的亲近性,产生了不少广受儿童欢迎的儿童文学作品。 而“照顾儿童阅读能力”的标准则得益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儿童文学作为“小学校里的文学”所具有的革新儿童教育的功能。以郑振铎为代表,将儿童文学作为尊重儿童特点的教育工具,以教育性作为儿童文学的根本特性,从而强调儿童文学与儿童阅读能力和阅读趣味的适配性。这种标准一方面强调儿童文学作为一种新式教育在思想内容上的独特与先进,要求“内容适合于儿童的年龄与智慧,情绪的发展的程序”⑨,反对“顺民或忠臣孝子的教育”⑩,且拒绝将儿童视作原人,将“神话、传说、神仙故事等”“人类的童年时代的产物”,“野蛮时代的‘成人’的出产物,全都搬给了近代的儿童去读”(11)。另一方面,强调成人对作品的改编技巧,务必契合儿童的理解能力和阅读兴趣,从而达到意义传达与接受的良好效果。郑振铎在《儿童文学的教授法》中引用了美国儿童文学理论家提出的三项原则,要点为:一、“应适宜于儿童的性情和习惯”“趣味和嗜好”;二、“所用的地名物名人名”须为特定儿童接受者所熟知;三、“新奇而不费解释的事物”“不妨尽量引用”以“扩充儿童智识范围”,“迎合他们的好奇心”(12)。可以看到,从教育工具角度出发的批评标准,是将儿童作为文本接受者来看待,以文本意义及传达的便利性和有效性作为评价儿童文学好坏的标准。它也强调儿童文学的特殊性,只是并不将其限定为对儿童生活心理的了解和再现,而是基于对儿童阅读心理和状况的把握,因时制宜迎合儿童的阅读视野,从而增加文本的亲和性,降低阅读理解难度,吸引儿童自主阅读接受,最终达到成人开发拓展儿童智识的最终目的。相比以儿童审美气质为审美境界追求的浪漫抽象,此标准更讲求实证性和技术操作性。其一,它注重对现实读者需求的客观把握,如1931年徐锡龄对不同年龄、性别儿童阅读兴趣的调研和实证研究(13)。其二,注重文本编写策略,迎合儿童兴趣,便于理解记忆,以保证教育信息被主动接收并留下印象。如20世纪30年代左翼作家华汉指出:“儿童读的东西与成人读的不同,儿童读物应该要有趣味——当然仅仅是技术上的趣味。”(14)钱杏邨、田汉、叶沉、沈起予、冯宪章、周全平等左翼作家亦提倡征求小朋友意见,了解少年趣味,并提出诸多如文字通俗浅显,多加色彩、插画,多用注音字母,多加歌曲等具体可操作的文本编织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