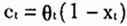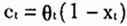问题的提出 在许多人的意识中,透明(Transparency)即使不是民主的同义词,也是民主的先决条件。如果社会不能普遍观察或者监管政策制定者的行为,他就有可能制定出违背大多数人利益的政策。他可能牺牲更广泛群体的利益来创造和分配对他(她)的家庭、朋友、支持者或者自己有好处的租金。没有了清新透明的监管环境,在乌烟瘴气的办公室中制定出来的政策,便不再服从于“人民”的意愿了。 模糊的、不透明的政策制定机制使得违背投票者意愿的寻租和资源浪费的行为更加便利。从另一个角度说,透明使得民主选举出来的政策制定者要接受选举人不受约束的问责,从而限制了租金的创造和转移。选举产生的官员如果还是照例将资源划于自己的名下,被发现的话,就会被选民赶下台。选举正是充当了这样一个角色,用来反映与政策制定者行为有关的信息。 透明是投票者的一种需求,如果没有了透明,官员就没有那么害怕被选民驱逐出办公室,就更有可能渎职。 但是需求仅仅是一个方面。如果政策制定者主动提供透明,我们就要考虑他提供的动机是什么。透明要求政府官员的意愿服从于投票者的监管。透明还要求建立一个自由获取信息的机构,一个产生信息的机构,这些可以用来限制政府官员利用他们的权力来隐藏他们的(贪污)行为。因此,从博弈的角度来看,提供信息、政策透明对于政府官员来说也是激励兼容的。 政策并不是从虚无中产生出来的。新的制度在罗尔斯的“无知之幕”(Rawlsean veil)后面被制定出来,因为新制度的制定者不知道他们将来是管理者还是被管理者。当然,如果制定者知道他们很可能是进入政府工作,那么他们可能倾向于设置更少的监管机构,从而给谋取私利带来更多可乘之机。于是民主政治出现了,人们不断制定出各种规章制度,其中也包括对透明的要求。而且这些透明的制度不仅仅要得到被管理者的赞同,还必须得到管理者的认同。因此,我们不禁要问:什么时候政策制定者会选择一种透明的机制呢? 这篇文章研究了在什么条件下透明对于政府官员也是激励兼容的(译者注:对于政府官员也是有利的)。那些需要接受投票者更多问责(译者注:也就是更大程度上受到投票者限制)且害怕被赶下台的官员,在整体经济形势萧条的时候会选择更大的透明度,并创造出更好的监管他们业绩的机制。每隔一段特定的时间,政府官员就要进行换届选举,这样民主政治被认为更加的透明。受投票者限制更小一些的政府官员则可能在政策制定过程中选择不透明的策略;独裁政治下的官员则不会关心选民的利益,他们可以安全地渡过经济萧条期,不用担心会被赶下台。 这篇文章也试图区分出透明和问责对于民主政治的其他两个方面的影响。我们将着重于官员的腐败水平和他们任职期的长短。我们认为,透明和解释义务对于腐败水平具有独立(于民主)的影响——民主可以减少腐败,如果再加上问责,则可以使腐败程度进一步降低。当民主制度进一步深入的时候,政策制定者力保自己地位的能力也会降低——独裁者往往可以长期任职,而民主人士只能企盼着能够通过下一次竞选连任下去。但是我们也可以预测,政策制定者越是能够连任下去,他们制定政策的过程就越透明。 在下面的模型中,政策是在不确定的情况下制定出来的。因为政策是在选举之前选定的,而政策制定者在选举的时候还不能够确定经济的总体形势。选民可以观测到自己的财富状况,却不能将政府官员选择的政策(内生变量)产生的影响和总体经济形势的影响(外生变量)区分开来。如果经济形势好,政府官员也没有从中谋取很多私利,投票者就会发现钱包鼓起来了,于是再次投票选举他。相反,如果总体经济形势不好,即使政府官员没有从中谋取过多的利益,投票者也可能投反对票。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个例子中的政府官员被不公正地赶下台了——他只是谋取了一小部分私利,只可惜外生的经济形势没有与他合作。 显然,那些很大程度上由选民选举决定的政府官员更加害怕被这样“不公正”地赶下台。而更少接受选民问责(民主程度更低)的官员则会倾向于谋取更多的私利,也不用那么担心被革职。 另一方面,如果政策制定是透明的,投票者就可以更好地将震荡与政策区分开来,也就不会当经济萧条时就处罚政府官员,而只是处罚官员谋取私利的行为。被选举出来的官员为了消除被不公正革职的风险,可能会选择放弃一些谋取私利的机会。因此,我们认为,政府官员为了增大其留任的可能性,会更加关注于选民的利益,也更有可能选择透明的政策制定形式。 这就产生了三个预测: 1.民主政治更可能产生透明; 2.政策制定者的任职期随着选民问责的增加而缩短,但是随着透明度的升高而延长; 3.腐败的程度随着透明度和问责的升高而降低,而且两个因素产生的效应是独立的。 模型 根据佩尔松、罗兰和塔贝里尼(Persson,Roland and Tabellini,1997)以及弗雷约翰(Ferejohn,1986)的观点,我们考虑这样一种政体,投票者每一任期消费一种公共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