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大学机构用户,欢迎您!
1920年10月创刊的《上海伙友》周刊,是上海工商友谊会的机关刊物,所载文章形式活泼,体裁多样。该刊主要面向店员发行。初期曾受中共影响,后转而宣传社会改良主义和劳资调和论。透过该刊“店员来信”,可以从中看出当时店员复杂艰辛的生存状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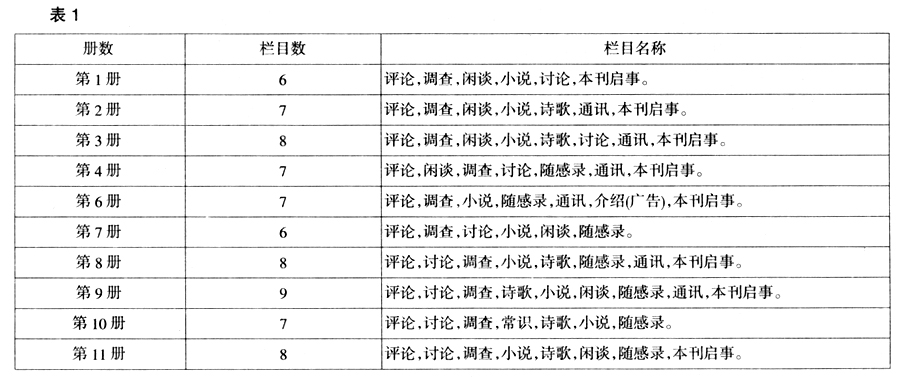 闲谈、讨论、随感录侧重于店员自身陋习的反省:态度恶劣,顾客进店,仍旧“拱手、谈天、玩笑、摇扇、吃食、趴卧”,不愿意做小生意,“我代朋友买纽扣两颗,某洋广杂货店,挂着照样的纽扣许多,三十岁左右的店伙问我买几颗,听说两颗生意买不来”⑧;以貌取人,对于生的漂亮、穿得体面的女子,便特别殷勤,虽被他骂几声“死人”、“杀千刀”,也喜形于色⑨。而对于衣衫褴褛,面黄肌瘦的男女不和颜相待,“讨厌讨厌,这种阿木林,也来买物,有玷我们的店堂不打紧,打断我们的话头,真真可恶”。痛苦是不力行的结果,“伙友受资本家的束缚,十分之三的人是咎由自取”⑩。 通讯是刊物与读者交流、互动的平台。《抱小孩是不是学徒应该做的?》、《无理底干涉》在抨击店主、经理的同时,反映了“伙友是最大”的办刊立场。《看新出版物的痛苦》、《伙友解放危险底讨论》、《女工为什么不能入会》既驳斥“八小时工作、八小时学习、八小时休息制度在中国行不通”的说法,又注重店员“解放”的路径引导,“不可怪新型出版物,要怪社会那班造恶的人”(11)。 二、《上海伙友》的发行量、传播渠道及影响 传播媒介的发行范围与销量,某种程度上可以反映出它的传播效果与影响力。关于《伙友》的发行量,相关研究论著及回忆录中都没有专门的统计,只是《本刊启事》中有较零星的记载,“会友担任承销者数百份,现售者亦数百份”(12)。而当时报刊的发行量通常在三千份左右,一些地方性报纸只有千余份甚至几百份(13),鉴此可知,《上海伙友》的发行量尚没有超出地方报纸千余份的界限。同时,“上海《伙友》的上海二字并不是说我们有地域之见,上海的伙友觉悟了自可影响全国,诸君不可误会”(14),《伙友报》第二期刊发的杭州某店员来信——《苦力人语》,无疑是刊物发行范围的一个佐证。 《上海伙友》最初由新青年社代为发行,并“拟定本埠各烟纸店代为销售”(15),当然也利用邮政、航运等运输渠道先运往各地,再通过书社和代派所传播,“留下详细地址,已备邮寄”。同时发动伙友,探索个体推销的传播路径,“由各伙友量力推销”。“我取了数十本《伙友周刊》去卖,不到半个钟头就卖完了。”(16)这一销售传播网络反映出《上海伙友》以上海为主兼向各地延伸、传播的受众范围。 发行量、传播销售网络是反映报刊传播效果的重要因素,《上海伙友》千余份的发行量,相较于人数众多的店员来讲(17),影响效果自不应无限夸大。很多店员甚至对《上海伙友》缺乏基本的了解,“我们去推销刊物,他们不要,还视我们为流氓”(18);“伙友愿意掏三角钱去看《…秘史》、《…艳史》等,不愿意两个铜板的《伙友周刊》,可怜”(19);“一个银行的伙友,说我们是过激党,扰乱分子,不仅不允许兜售反而破口大骂”(16);“我们是做生意的,不是读书人,汝要卖与那读书人去看好哩”,“我不要看这些书,我看汝这书,不会买些报纸来看看”(20)。此外,从传播学的角度来讲,由报刊传递的印刷符号信息,必须准确还原才能发挥影响力。1920年代,禁止店员阅读书报是普遍行为,“私阅闲书小说及购小报者,罚洋五元”(21),部分店铺尽管标榜科学管理,规定“中餐后一小时内可以读报书”,但《上海伙友》是“过激刊物”,不在允许之列,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其传播效果。
闲谈、讨论、随感录侧重于店员自身陋习的反省:态度恶劣,顾客进店,仍旧“拱手、谈天、玩笑、摇扇、吃食、趴卧”,不愿意做小生意,“我代朋友买纽扣两颗,某洋广杂货店,挂着照样的纽扣许多,三十岁左右的店伙问我买几颗,听说两颗生意买不来”⑧;以貌取人,对于生的漂亮、穿得体面的女子,便特别殷勤,虽被他骂几声“死人”、“杀千刀”,也喜形于色⑨。而对于衣衫褴褛,面黄肌瘦的男女不和颜相待,“讨厌讨厌,这种阿木林,也来买物,有玷我们的店堂不打紧,打断我们的话头,真真可恶”。痛苦是不力行的结果,“伙友受资本家的束缚,十分之三的人是咎由自取”⑩。 通讯是刊物与读者交流、互动的平台。《抱小孩是不是学徒应该做的?》、《无理底干涉》在抨击店主、经理的同时,反映了“伙友是最大”的办刊立场。《看新出版物的痛苦》、《伙友解放危险底讨论》、《女工为什么不能入会》既驳斥“八小时工作、八小时学习、八小时休息制度在中国行不通”的说法,又注重店员“解放”的路径引导,“不可怪新型出版物,要怪社会那班造恶的人”(11)。 二、《上海伙友》的发行量、传播渠道及影响 传播媒介的发行范围与销量,某种程度上可以反映出它的传播效果与影响力。关于《伙友》的发行量,相关研究论著及回忆录中都没有专门的统计,只是《本刊启事》中有较零星的记载,“会友担任承销者数百份,现售者亦数百份”(12)。而当时报刊的发行量通常在三千份左右,一些地方性报纸只有千余份甚至几百份(13),鉴此可知,《上海伙友》的发行量尚没有超出地方报纸千余份的界限。同时,“上海《伙友》的上海二字并不是说我们有地域之见,上海的伙友觉悟了自可影响全国,诸君不可误会”(14),《伙友报》第二期刊发的杭州某店员来信——《苦力人语》,无疑是刊物发行范围的一个佐证。 《上海伙友》最初由新青年社代为发行,并“拟定本埠各烟纸店代为销售”(15),当然也利用邮政、航运等运输渠道先运往各地,再通过书社和代派所传播,“留下详细地址,已备邮寄”。同时发动伙友,探索个体推销的传播路径,“由各伙友量力推销”。“我取了数十本《伙友周刊》去卖,不到半个钟头就卖完了。”(16)这一销售传播网络反映出《上海伙友》以上海为主兼向各地延伸、传播的受众范围。 发行量、传播销售网络是反映报刊传播效果的重要因素,《上海伙友》千余份的发行量,相较于人数众多的店员来讲(17),影响效果自不应无限夸大。很多店员甚至对《上海伙友》缺乏基本的了解,“我们去推销刊物,他们不要,还视我们为流氓”(18);“伙友愿意掏三角钱去看《…秘史》、《…艳史》等,不愿意两个铜板的《伙友周刊》,可怜”(19);“一个银行的伙友,说我们是过激党,扰乱分子,不仅不允许兜售反而破口大骂”(16);“我们是做生意的,不是读书人,汝要卖与那读书人去看好哩”,“我不要看这些书,我看汝这书,不会买些报纸来看看”(20)。此外,从传播学的角度来讲,由报刊传递的印刷符号信息,必须准确还原才能发挥影响力。1920年代,禁止店员阅读书报是普遍行为,“私阅闲书小说及购小报者,罚洋五元”(21),部分店铺尽管标榜科学管理,规定“中餐后一小时内可以读报书”,但《上海伙友》是“过激刊物”,不在允许之列,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其传播效果。